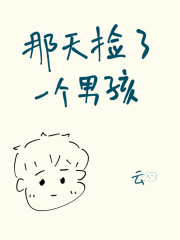父亲那句“一个人当着你的面或许可以轻松伪装本心,可在画里他伪装不了。人的心若是不纯净,他的画肯定也是脏的,而于翔潜的本心绝对干净”,跟电量不足的老收音机一样一直响在她耳旁。温喜兰无助的叹了口气,确信自己没办法让父亲改变主意。想到这里,她不争气的回头看了一眼。...
《囍冤家》精彩内容
主角是于翔潜温喜兰的小说叫《囍冤家》,这本小说的作者是佚名创作的短篇言情类型的小说,书中主要讲述了:父亲那句“一个人当着你的面或许可以轻松伪装本心,可在画里他伪装不了。人的心若是不纯净,他的画肯定也是脏的,而于翔潜的本心绝对干净”,跟电量不足的老收音机一样一直响在她耳旁。温喜兰无助的叹了口气,确信自己没办法让父亲改变主意。想到这里,她不争气的回头看了一眼。......
温喜兰双臂抱在胸前冷眼看着,于翔潜捂住嘴两眼含泪,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仪容,似乎还想对她说教,可已经完全没了刚才居高临下的气势。
“这个婚,我不结了!”最后,于翔潜含混不清的扔下一句话,捂着嘴就往外面走。
“不结就不结,正好!”温喜兰捡起自己的包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。
可刚走出去二十多米,温喜兰又停住了。今天要是不跟于翔潜领结婚证,回家怎么跟父亲交代?
就算把于翔潜刚才的话背一遍给父亲听,他能相信吗?他至始至终都沉浸在“画如其人,人如其画”论断里。
父亲那句“一个人当着你的面或许可以轻松伪装本心,可在画里他伪装不了。人的心若是不纯净,他的画肯定也是脏的,而于翔潜的本心绝对干净”,跟电量不足的老收音机一样一直响在她耳旁。
温喜兰无助的叹了口气,确信自己没办法让父亲改变主意。
想到这里,她不争气的回头看了一眼。
巧的是,于翔潜也停住脚步在回头看她,那双眼,愤怒中夹杂着仇恨,还有和她一样的无助。
嗯…他确实不是个善于伪装本心的人。
于翔潜此刻的心情也糟糕透了,他完全不想跟这个温喜兰结婚,方才说出那样难听的话,目的就是想气走温喜兰。
可是,可是如果不娶温喜兰的话,他的香雪怎么办?还有翠影、秋月、夕颜…通通会被赶出家去流落街头…
两个人就这样各自用充满恨意的眼睛对视了两分钟,而后同时转身往民政局里走去。
“开——席——喽!”
随着透亮的一嗓子,十几个系着红围裙的男人,手里托着装满硬菜的大盘子,一脸喜气走进了宽敞的老四合院。
头鸡、二鱼、三丸子,图个吉利、富足、圆满的好寓意。
今儿是阳历6月10号,农历5月初7。老黄历说,宜嫁娶。
温喜兰穿了一身大红旗袍,头发盘了起来,簪了红玫瑰满天星花束,上了妆的脸少了几分少女灵动,多出些成熟稳重。
于家是做文房四宝生意的,做事风格比较传统,坚持认为结婚这样大喜的日子就该穿喜庆的红色,旗袍最合适。于家二老看不惯西洋风格的白色婚纱,温贤也是。
“嗨,我说于叔,今儿是你家于翔潜娶媳妇,咋就看见新娘子,没看见新郎官呢?”一个吃的满嘴是油的中年男人冲着正堂位置直嚷嚷。
“说的是呢!”一个中年妇女也跟着附和:“新娘子长得周正讨喜,面相一看就是旺夫的!新郎官本来就长得俊,县里再也挑不出第二个,大喜的日子金童玉女才子佳人,咋少了半边儿?”
本来闹哄哄的院子,被两人一问,瞬间安静下来。
原本所有人都只顾着大快朵颐,毕竟大家的生活水平都不高,平常就算过年也吃不上这么丰盛的酒席,谁也没在意新娘旁边没新郎。
再说了,谁家结婚是一个人?一个人能叫结婚?
此时所有人的眼睛都看向坐在正堂的当家人于千山,转而又瞥向新娘温喜兰。
于千山的脸色不好看,家里的独苗结婚,这是“祥宝斋”的喜事,更是于家的大喜事,可于翔潜这小兔崽子偏偏不给他省心。于千山拉着脸,轻咳一声刚要开口,就听院子里又有人起哄。
“别不是昨个晚上提前入了洞房,今天下不来床了吧?!”
他这句话一落下,于千山腾的就站起来了。
于家在陵澜是正儿八经的书香门第,祖上还出过举人,这附近十几个县市的宣纸、砚台、墨汁墨块几乎全是祥宝斋在供应。
陵澜附近有句老话:再穷的人家家里也能翻出一筐祥宝斋的文房四宝。
有人在于家的喜宴上说这样的浑话,那不是往于千山脸上泼洗脚水吗?
眼看老爷子一脸铁青的从正堂走出来,满院宾客都紧张了,手里的筷子,举起的酒杯又悄悄放了回去,方才说浑话的人脸都吓白了。
“您也知道今天是大喜的日子,”温喜兰不慌不忙的也跟着走了出来,规规矩矩的跟在于千山的身后,冲着脸白的男人温声道:“既然是大喜的日子,多喝两杯少说两句,您要是不满意,一会儿我替于翔潜多敬您两杯酒就是了。”
来吃席的人里不乏眼皮子活的,眼看新娘子亲自铺台阶,哪能不接着?今天满院子的宾客,不给谁面子也得给新人面子。
而且这面子,于千山也得给。
“对对对!新娘子说的对!咱们一年到头累死累活,还没吃过这么丰盛的酒席,于家办喜事,咱们都跟着沾光了,来来来,都端起酒,咱们一起敬于叔一杯!祝新人白头到老,祝于家生意兴隆!”
于千山明显被突然转变的情况弄得有点懵,憋了一肚子的火是不能发了,满院子的人敬酒,唯独他两手空空。
“爸,您的酒。”温喜兰把满杯的酒递进他手里。
连干三杯以后,院子里又热闹起来,于千山也和颜悦色的回到座位上。
温喜兰则在媒人大姐的陪同下去给宾客们敬酒。
几桌走下来,长辈们对她赞不绝口,同辈的女人们也愿意拉着她多说几句,俨然已经把她当成了常走动的亲戚。
当走到靠中间一桌的时候,一位高个子男人突然拽住她的胳膊。
“我说弟妹,你刚才可是说了,要替于翔潜多敬我两杯酒,轮到我们这桌了,你可别怯场!”
温喜兰仔细一看,正是刚才说浑话的男人,没想到方才被老爷子吓得不敢吭声,这会儿见她身后没了撑腰的,又要蹬鼻子上脸了,完全不记得刚才是谁帮着解围。
“我说李三两,你怎么就是不长记性呢!”
不等温喜兰说话,媒人大姐先一把拍开他的爪子,警告道:“你要是再找茬,小心那边于叔把你打出去!”
“大喜的日子哪有打人的?喜酒嘛当然得多喝几杯!”李三两梗着脖子反驳,转而又换了个笑脸看向温喜兰:“你说是吧,弟妹?”
眼见他又要没个分寸,一旁的中年妇女用力拉他一把:“行了孩他爸,你今天又喝多了,可别丢人现眼!”说罢妇女一把他推到后面,拉着温喜兰的手满脸歉意的道:“弟妹,别跟他一般见识,他这个人一沾酒就爱胡说!”
“谁胡说?说谁呢?你看哪家妇女这么褒贬自家老爷们儿的?”李三两瞪起眼将妇女一把推了个趔趄,惊得一圈儿人一阵唏嘘。
媒人大姐连忙把温喜兰护在身后,撸起袖子要跟他撕扯。
《囍冤家》最新文章
- 第一章小说无广告阅读 魏书言苏沐禾小说
- 周扬唐念的主角名小说叫什么
- 我留下一纸离婚书后妻子后悔了完整版在线阅读(主角周扬唐念)
- (爆款)周扬唐念大结局小说全章节阅读
- 匿名新书我留下一纸离婚书后妻子后悔了在线阅读
- 周扬唐念小说无广告阅读
- 【新书】《我留下一纸离婚书后妻子后悔了》主角周扬唐念全文全章节小说阅读
- 大小姐的王牌保镖 第十七章 满身都是优点的男人
猜你喜欢
- 冤家
- 宁总
- 徒弟
- 一品女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