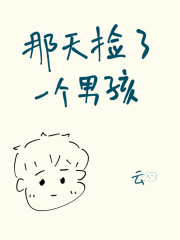我想会的,无论出于什么。我妹妹被逼跳楼后,我再也没有回过家,甚至不会再和他们打电话发消息。妹妹过世的第六年,他们突然给我打了一大笔钱。我这才接通了他们的电话。
《穷极一生的治愈》精彩内容
小说主人公是程欢程欣的书名叫《穷极一生的治愈》,它的作者是佚名所编写的现代言情风格的小说,内容主要讲述:我想会的,无论出于什么。我妹妹被逼跳楼后,我再也没有回过家,甚至不会再和他们打电话发消息。妹妹过世的第六年,他们突然给我打了一大笔钱。我这才接通了他们的电话。...
我想会的,无论出于什么。
我妹妹被逼跳楼后,我再也没有回过家,甚至不会再和他们打电话发消息。
妹妹过世的第六年,他们突然给我打了一大笔钱。
我这才接通了他们的电话。
是微信视频,那两张脸苍老了很多,一时让我觉得很陌生。
他们摆给我的笑脸,和小时候他们摆给客人看的很像。
他们说,他们查了我这边的房价,挺高的。所以他们把目前所有的积蓄都给我了,让我全款买个房,他们也安心。
见我不言不语,我妈连忙补充说:「我们以后也不过去,就在这儿活到老了。你要是之后遇到好男孩,该谈也谈谈。需要爸妈帮忙的,就尽管说。」
「尽管说啊,欢欢。」
我把钱全部退给了他们。
「没事儿就别联系了。也别给我打钱了,不然我彻底拉黑你们。」
我挂了电话,躺在床上。
以前我们家也是很幸福的。
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,再也不可挽回了呢?
在我的印象里,我爸是在我妹出生之后开始酗酒的。
他是大学老师,喝了酒也会保持风度。起初夜里醉酒回来,只会在客厅沙发上蒙头睡下,任凭我妈怎么责备,都默不作声。
后来,他再喝大了回来,就会和我妈顶嘴了。再过两年,他甚至敢叫同事们来家里喝酒。趁着酒劲儿,大声数落我妈的不是。
但当着外人,我妈一直很给我爸面子。她会笑着认错,道歉的样子也和有风度的富家太太一样。
非得客人夸我们家真是书香门第才罢休。
我妈其实也不差。那个年代,她是很少的研究生毕业学历,到我快高考的时候,她就已经坐上了体制内正处级的位置。
当时她的好些同事、朋友订了酒席给她庆贺,不过她并没有带我。
因为我中考考砸了,读的高中不是市里最好的,位置偏得都快出城了,她觉得丢人。所以她给大家编了个谎言,说是我学校不让住校生周末出来。
这事儿还是我妹告诉我的,她的原话是:「妈妈说想去接你,但是你的老师不让。」
那会儿我高三,程欣比我小十三岁,在读幼儿园。
我看着她钝圆的眼睛,只是摸了摸她的头,跟我妈一起骗她:「嗯,对呀。」
但我还挺庆幸我中考考砸了,那样我就能住校了。因为那会儿,我爸妈吵架已经变成家常便饭了。
我戴着耳机听英语,程欣放着汉语拼音的教学光盘,音量调到最大声都盖不住。
吵也无所谓,我们也习惯了。可是他们吵架的内容,总是让我坐立不安。
或许程欣也会坐立不安。只是我一直误以为她那会儿很小,什么都不懂。
因为来去不过就是两个话题——我,程欢;和我妹妹,程欣。
我爷爷奶奶是山沟里的老农民,一直很重男轻女。
我出生的时候,我爷爷一知道我是女孩,当时就跌坐在了凳子上。我奶奶一眼都没看我,趁我妈还清醒的时候说:「过几年再生一个儿子。」
那会儿还是独生子女的政策,当然不行,我妈也不愿意,所以两辈人闹得很僵。
这些事儿,是我妈告诉我的。
在我高考的前两个月,我爸头一次酗酒到夜不归宿,她在卧室抱头痛哭,我想去安慰她,她砸着床头柜对我说了这些事。
我爸倒并不重男轻女,甚至一直以来比我妈对我更好。
我还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,他每周送我去学大提琴,上完课都会带我去买个炸鸡腿吃。
我妈说只准我学得好、被老师奖励了小发夹的时候才能吃。但我爸每周都会给我买,没有小发夹的日子,就仔仔细细帮我擦干净嘴,和我心照不宣地瞒我妈。
有时候作业错题多,我妈逮着我骂的时候,他也会帮我说几句话,赶我去睡觉前,把热好的牛奶塞到我手里。
所以那几年,虽然爷爷奶奶的事儿横亘着,我爸妈倒不会吵起来。只是每年过年,我妈都绝不同意我爸把爷爷奶奶接来住几天。
我爸带我正月里回老家拜年,我妈也从不会跟着一起去。一次也没有。
可如果有人问起,我妈会欺骗他们说,每年我们一家三口都会在爷爷奶奶家待好几天。而那几天她会一个人窝在家里,闭门不出。
我很难想象,她是用怎样的心情,做贼一样度过那些独处时光的。
小升初的时候,我考上了本市最好的初中。我其实挺开心的,尤其语文和数学两科,都算超常发挥了。
但我爸说,他就是教数学的,我总不能数学考不好吧。我妈说,我好在考上了,不然她当初白托人让我上那么好的小学了。
其实日子到这里,虽然我心理压力一直很大,但家庭还算和睦。爷爷奶奶这么多年也看开了很多,甚至有和解的趋势。
但刚好就在我念初一这一年,国家出了新政策。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话,城市户口也可以生二胎。
于是老话重提,他们开始了无休止的争论。
我一直以为我们家感情很好,来家里做客的叔叔阿姨都这么说。
每年寒暑假,我爸妈都会带我去没去过的地方玩儿。每个地方留一张合照,就装在电视柜下的相册里。
相片里一家三口相拥着,看着是很好啊。很好很好啊。
直到他们为了二胎这个事儿,谈条件的时候。
我头一次冒出这种奇怪的念头:我们不是一家人在生活,而是三个人在搭伙。
他们原本是有意识避着我的,之后闹得频繁了,当着我的面在饭桌上就能吵起来。
那个新年我过得如坐针毡。
我低头扒拉年夜饭,电视里传出喜庆的音乐,我妈把筷子砸在我爸脸上:「我都三十六岁了,你想没想过这对我有多危险?」
我爸也放下了碗筷,始终低着头,「现在的医疗和护理条件都很好,无非就是多花些钱的事。你只管生,钱都我出行吗?」
「生了儿子就算了,再生个女儿你和我离婚怎么办?这些年我的钱全给你这个女儿花了,又要吃又要穿,你知道那些课外班多贵吗——」
我妈说这话时,右手食指狠狠戳了戳我的后脑勺。
「我连套房子都没有,到时候你让我拉着两个女儿出去要饭吗?」
我实在没忍住,哭了。也不敢哭出声,借拿纸擦嘴抹掉了眼泪。
我爸本来身子坐直,还想理论什么。可大概是因为看见了我的可怜样子,又重重靠在了椅背上。
最后是用房子换了儿子。我爸答应过完年就带我妈去办过户手续——是我爸婚前买的一套房,这几年一直租出去的。
我们现在住的是学校分给我爸的房,去年才盖好的新楼。临着一条河,十七层往外看,夜景很好。
只是后来,我几乎再没静下心来好好看过那边的景色。
只记得那些刀痕一样的争吵,将明净的窗玻璃划得斑驳细碎。
《穷极一生的治愈》最新文章
- (爆款)沈士坤俞雯大结局小说全章节阅读
- 错爱成灰,缘尽无回by麦穗儿在线阅读
- 《错爱成灰,缘尽无回》by麦穗儿
- 错爱成灰,缘尽无回by麦穗儿 沈士坤俞雯免费阅读
- 贺君轩沈梦月小说无广告阅读
- 至尊霸婿未删减阅读
- 小说至尊霸婿txt全文在线阅读
- 至尊霸婿
佚名其他作品
猜你喜欢
- 治愈
- 失宠
- 殿下
- 异界